译者:末夏
克莱尔·韩德斯康上网时总是无法投入。就像许多网络冲浪者一样,她点开PO在社交网站上的链接,读上几句,搜寻激动人心的字眼,接着便不耐烦起来,直接跳到下一个她多半同样看不进去的页面。
“我只会看个几秒钟——连几分钟都嫌多——然后就又去看别的了。”韩德斯康说,35岁的她是美国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研究生。
但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上网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读小说时也是如此。
“就好像你的眼睛掠过那些字词,但你却领会不了它们表达的意思。”她坦承,“当我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我只好倒回去一遍遍地读。”
在认知神经科学家看来,韩德斯康的体会既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人类,他们警告道,似乎在飞速浏览网络信息洪流的过程中发育出了拥有全新回路的数字化大脑。
“我担心在我们阅读需要更加深入理解的东西时,会受到白日里那种肤浅阅读方式的影响。”塔夫茨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家暨《普鲁斯特和鱿鱼:阅读脑的科学与故事》一书的作者玛丽安妮·沃尔夫说。
沃尔夫指出,如果说全日无休的付费电视新闻的崛起,在全世界营造了一种音节文化,那么互联网带来的就是眼睛的字节文化。根据追踪数字化行为的eMarketer公布的数据,2013年美国成年人每天在网上消磨的时间——通过台式计算机或移动设备——料将超过5个小时。相比2010年的3小时上升。
阅读爱好者和科学家们借鉴“慢食”运动的招牌,发起了“慢读”运动。他们反对的不单是走马观花的阅读方式,还有潜伏在电子设备上诱惑着我们,无休无止的社交媒体更新和电子邮件——那些叮叮当当的提示音,让人连“叫我以实玛利”都读不下去。(译注:此为赫尔曼·梅尔维尔小说《白鲸记》第一章第一句)
研究人员正在努力了解阅读网络文字和阅读印刷文字的差异——刚开始阅读的人对纸本的理解能力似乎更好——并设法弄清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人们享受阅读最新小说的乐趣,以及理解工作和学习上的难懂材料。有人担心,幼儿粘着家长的电子设备不放,甚至常常将之据为己有,可能会阻碍其深层阅读能力的发展。
大脑是这个新鲜世界的无辜旁观者,它只是反映我们如何生活。
“大脑终其一生都是可塑的,”沃尔夫说,“它一直在不断适应变化。”
沃尔夫是全球阅读研究的一流专家之一,去年,她发现自己的大脑显然也在适应新变化时,大吃一惊。一天晚上,在一整天都在浏览互联网和数百封电子邮件之后,她坐下来读赫尔曼·黑塞的《玻璃珠游戏》。
“不是说笑:我竟然做不到,”她说,“我万般痛苦地读完了第一页。我没法强迫自己慢下来,不要只是略略读过,拣出关键字,转转眼珠子,用最快速度生成信息。我简直恨死自己了。”
适应阅读
大脑并非天生就为阅读而设。不像语言或者视力,阅读是没有基因的。然而,受埃及象形文字、腓尼基字母、中国纸以及总算出现的古腾堡印刷术刺激,大脑已经适应了阅读。
在互联网出现前,大脑基本上是以线性方式阅读——一页接着一页,诸如此类。当然,文本或许配有图片,但基本上没有太多干扰。研究人员说,阅读印刷文字甚至让我们掌握了一种超凡的能力,只需观察文字的排篇布局就知道关键信息位于何处。读完整整一页相关对话之后,我们一看到下一页上有两大长段,立马就明白有个主角是要死在这儿了。
互联网则全然不同。那么多信息,超链接文本,视频边上的说明文字和互动设计比比皆是,我们的大脑形成了一种处理它们的快捷方式——扫读,搜寻关键字,快速上下浏览。这就叫非线性阅读,已经被记录在了学术研究中。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许多人在与其他媒介打交道的时候也受到这种阅读方式的干扰。
“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触摸屏幕,推送,链接,滚动鼠标,跳着阅读,当我们坐下来捧起一本小说的时候,已经摆脱不了跳跃式阅读、点击鼠标、链接的日常习惯了。”得克萨斯大学的阅读研究人员狄龙说。“我们身处一个信息行为的新时代,后果已经开始显现。”
31岁的布兰登·昂布罗斯是一名海军金融分析师,住在Alexandria,他深知这些后果。
他所在的读书俱乐部最近阅读了梅格·沃丽泽的畅销书《夏令营的孩子们》。当书友们碰面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书中不少关键情节点。这件事让他猛然醒悟,自己一直是在扫读这本书,搜寻某一特定方面的信息,就如同一天中的大多数时候,他坐在计算机屏幕前,搜寻某一特定事项一样。
“当你尝试阅读一本小说时,”他说,“情况简直就像我们再也不是天生就会阅读一样,就是这么糟。”
拉姆什·库鲁普发现了一些更加叫人不安的现象。近来埋首阅读多位经典作家——乔治·艾略特、马塞尔·普鲁斯特之类——47岁的库鲁普发现自己很难读懂那些跟着好几个繁复从句,充满了背景信息的长句。互联网上的句子往往较短,而那些包含了复杂信息的句子通常会链接至有用的背景材料。
“书里可没有图片或链接来让你跟上思路。”库鲁普说。
他认为,比起连篇累牍的长段落、长句子,跟着链接阅读更容易。
库鲁普的观察心得听起来似乎有点牵强,但他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之后,沃尔夫并未嗤之以鼻。她列举了更多例证:全国各地多名英语系主任发来电子邮件告诉她,他们的学生在阅读经典名著上遇到了困难。
“他们读不了《米德尔马契》。他们也读不了威廉·詹姆斯或亨利·詹姆斯。”沃尔夫说,“数不清有多少人写信告诉我这个现象。学生们再也不想,或者说,再也没法理解乔治·艾略特和亨利·詹姆斯错综复杂的语法和句子结构了。”
沃尔夫声明,她可不是卢德分子(译注,指害怕或讨厌技术的人)。她用iPhone发送电子邮件的频率不输学生。她参加慈善项目,向发展中国家赠送平板电脑以帮助那里的孩子学习阅读。但她接着说,只要看看推特和上面那些140个字符的轻快短句。
“这当中丢失了多少语法啊,语法是什麽,不就是反映我们错综复杂的思想吗?”她说,“我担心我们将失去书写或阅读这般繁复华美之文藻的能力。我们会不会变成推特脑呢?”
两用大脑?
沃尔夫的下一本书将研究数字化世界对大脑的影响,包括观察人们阅读网上文字和印刷文字时的脑部扫描数据。她特别感兴趣的是人们在屏幕上和纸本上阅读时的理解结果。
针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引人深思的研究。2012年,以色列的一项研究要求在屏幕世界里长大的工科学生分别在屏幕上和纸本上阅读相同的文本,并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学生们都以为在屏幕上阅读的效果更好。可他们错了。实际上,他们阅读纸本时的理解和学习能力都更优。
研究人员认为,应该对纸本阅读和屏幕阅读之间的差异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并在教育中解决这个分歧,尤其是在对学龄儿童的教育中。两种阅读方式各有优点,我们或许能够培养出两用大脑。
“我们已经无法回头,”沃尔夫说,“我们应该一边为孩子朗读书籍,一边让他们自己阅读纸本,帮助他们学会这种较为缓慢的阅读方式,与此同时,让他们逐渐增加与科技、数字化时代的接触。两者兼顾。我们必须问自己:什麽是我们想要保留下来的?”
沃尔夫正在训练自己的大脑同时适应两种阅读方式。第二天晚上,她重新捧起了黑塞的小说,并且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留出与屏幕的间隔和距离。
“我抛开一切,跟自己说,‘我必须这么做’。”她说,“第二晚真的很难熬。第三晚也是。我花了两周,但到第二周结束的时候,我差不多恢复过来了,于是我享受着阅读的滋味,读完了那本书。”
然后,她又读了一遍。
“我想要再次感受慢读的乐趣,”沃尔夫说,“当我找回自己,宛如大病初愈。我再度找回了缓慢阅读,细致品味与专注沉思的能力。”
文章末尾固定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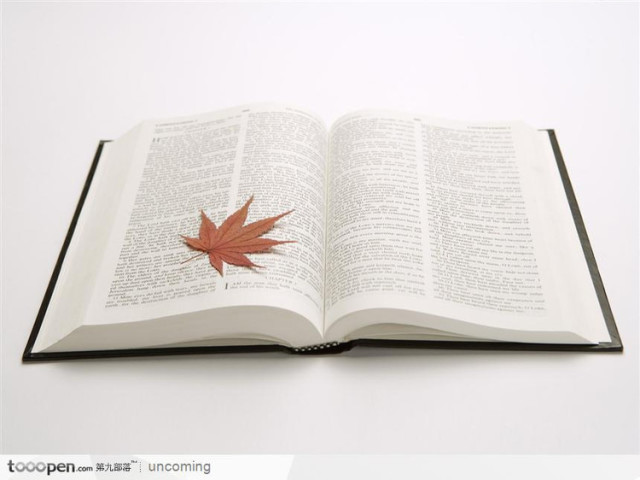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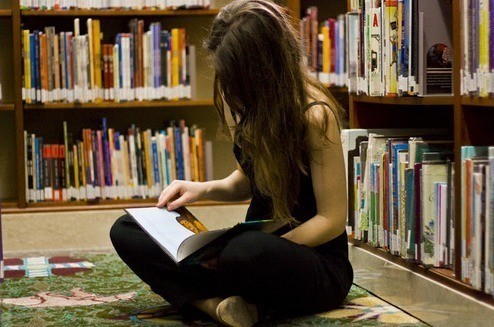
评论